



9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人民法院种业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典型案例。从2016年至2020年,全国各级人民法院审结涉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民事案件共781件,其中85%以上为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主要涉及玉米、小麦、水稻等主要农作物,超七成案件品种权人胜诉[1]。

图为发布会现场。胥立鑫 摄
对于种子或者说种业的保护,大多数国家包括我国主要还是依靠植物新品种权进行保护。育种是古老的,但是植物品种保护制度从诞生到不断完善也不到200年的历史。
从整个国际范围来看,对植物新品种的保护从最初的罗马教皇发布的声明到《美国植物专利法》的颁布再到UPOV的出台,是一个逐渐完善且适应生物技术发展和农业全球贸易扩大的结果。
从本期文章开始,德同智汇将从制度、实践以及未来发展三个角度与大家一起探讨如何更好地保护植物新品种以及运用新品种。
植物新品种
植物新品种是指经过人工培育的或者对发现的野生植物加以开发,具备新颖性、一致性、特异性、稳定性,并有适当的命名的植物新品种。植物新品种权便是指完成育种的个人或单位对其授权的品种依法享有的排他使用权。
在我国,植物新品种权的申请受理和审查由国务院农业、林业行政部门即现在的国家林草局负责,相关文件需要通过林草植物新品种保护网的林草植物新品种网上申请管理系统递交。
从管理部门上来说,植物新品种权的审查和授予并不由国家知识产权局管理。实际上,根据TRIPS协定二十七条第三款第二项“除微生物外的植物和动物,以及除非生物和微生物外的生产植物和动物的主要生物方法。”是属于协定成员可以拒绝授予专利权的客体之一。我国的《专利法》第二十五条也明确说明对“动物和植物品种”不授予专利权。
但是TRIPS协定二十七条第三款第二项同样规定了“各成员应规定通过专利或一种有效的特殊制度或通过这两者的组合来保护植物品种。”所以,我国对植物新品种权的保护是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进行保护。
纵观全球,植物新品种的保护大致经历了前UPOV阶段、UPOV1978和UPOV1991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2]。三个阶段的发展不仅是植物新品种保护越来越完善的阶段,实际上也是生物育种技术和全球贸易大发展的体现。
前UPOV阶段
作为一种古老的学问,和医药研究、开发类似,植物新品种的培育也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而且培育出来的植物新品种在形态、抗病等方面也需要有所突破,符合生产需求[3]。
早期人类根据经验进行育种,基本过程就是自然决定加人为选择。所以,通过选择育种形成的新的植物品种主要还是自然的产物,人所施加的干预活动以及在干预中形成的智力活动成果是很少的。
随着人为干预在育种中的增加,在育种中形成的智力活动成果却很难被保护,育种者无法有效防止他人繁殖自己培育出来的新品种。
最早保护植物新品种的相关制度是1833年罗马教皇发布的关于给予技术和农业领域所有权并保护的声明,该声明内明确表示“从1826年9月23日起,对于科学、文学工作的成果,对涉及农业及其更加可靠的技术和更加有效的方法成果授予专有权。”
随着西方农业的发展,机械化程度不断提高,化肥工业也得到了发展,农业逐渐成为世界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们对于种子质量的要求也逐步提高,品质优良的种子也逐渐成为推动农业快速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因此,育种开始有了专业化发展,种子生产和贸易逐渐成为较为独立的产业。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开始,育种技术理论逐渐发展出具有系统理论支撑和科学实验方法的一门应用科学,育种学家从事的创造植物新品种的活动逐渐被科学证实并被社会承认[4]。
伴随着育种技术的发展和植物新品种的增加,对植物新品种的保护的呼声也越来越强烈,美国、德国、英国、法国等国家开始探索如何为植物新品种提供法律保护,从而激励育种创新活动,推进农业等发展。
1930年《美国植物专利法》颁布,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授予植物育种者植物专利的国家法律。但是《美国植物专利法》保护的内容并不包括茎块培育的植物和未培育状态下发现的植物,并且认为无性繁殖是保持植物纯种的唯一方法。
再加之美国当时的种子产业为了各自的产业利益作出了不同的立法选择[5],因此,植物专利成了美国独有的知识产权保护形式,并未被其他国家借鉴。
同时期,欧洲的也开始为植物育种创新提供保护。1883年法国先后通过《法国专科植物保护法》、实行检测、登记、颁布植物培育品种名录、登记与专利保护结合等方式对植物新品种进行保护。
1941年荷兰《植物育种法》,以PBR (Plant Breeder’s Right)的形式保护植物育种者的权利。1953年德国颁布并实施《栽培品种及种子保护法》并在法律中明确了活体植物保护的情况。
荷兰、德国、英国等建立的植物新品保护法律体系基本上都是以法国相关制度作为基础进行的,与美国此前已经形成的植物品种保护制度并不相同。
德国1953年颁布的《栽培品种及种子保护法》在设计、原则和框架上成为1961年UPOV公约的基础。1961年法国、联邦德国、荷兰、意大利、英国、瑞典等国在1961年签署UPOV公约,选择在专利制度外,专门创建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该公约于1968年8月10日经联邦德国批准后生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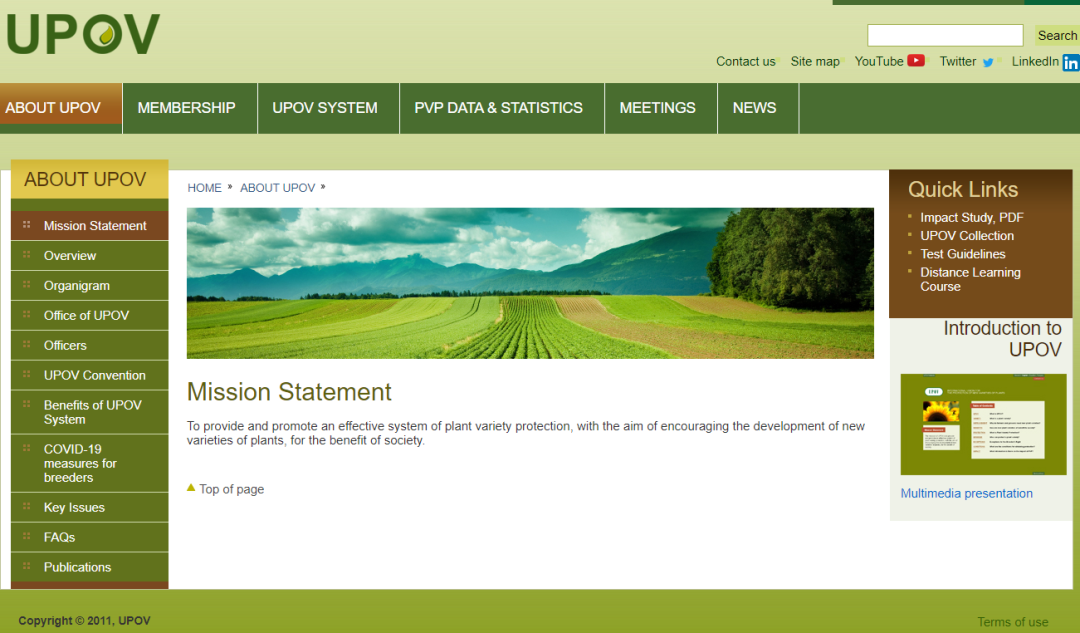
图:UPOV官网截图
截图:德同智汇
美国随后引进该制度,于1970年通过《美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法》为有性繁殖或块茎繁殖的植物新品种提供了保护。
UPOV1978阶段
水稻、小麦的矮化和抗病虫育种引发的“第一次绿色革命”[6]推动了世界农业的发展,也促进了作物育种学的发展[7],国际上对植物育种创新保护的需求日益强烈。
尽管UPOV公约缔约后,植物新品保护制度初步形成,但其认为品种权保护的客体是具备一致性和稳定性的栽培品种、无性系、品系、种群或杂交种[8]。
而且保护方式上,UPOV公约1961版和1972版都没有明确专利权和品种权之间的关系,并且与《巴黎公约》建立联系[9]。在1978年前,加入UPOV公约的除了南非均是欧洲国家。
考虑到上述情况以及全球种业发展和育种保护的必要性,UPOV公约于1978年10月23日进行了第二次修订。
UPOV1978增加双重保护禁止的例外规则(Exceptional Rules for Protection Under Two Forms)[10],删除了关于“品种(Variety)”的定义,增加了植物新品种保护的新颖性和稳定性要求[11],明确了以植物表型特征作为申请品种是否具有特异性、一致性和稳定性的判断要件,确定了DUS测试在植物新品种保护中的基础性地位,并且删除了UPOV公约与《巴黎公约》之间的制度联系,使得UPOV成为一个独立的国际组织。
UPOV1978的修订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更多国家的加入,另一方面也完善了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的基本内容,基本上确立了是否授予植物新品种权的几大判断要件,较1961版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
但限于技术发展水平和育种方式,UPOV1978对植物新品种的判断是以植物的表型特征作为基础,并没有考虑到基因层面的问题,并且只针对某一国范围内的市场,并未考虑到全球贸易的情况。
UPOV1991阶段
专利制度的完善与扩展,农产品国际贸易的扩展,生物技术的发展和产业化,基因技术和全球农业、种业合作与竞争的加强,使得UPOV1978所设立的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很难再适应新的挑战。
首先,UPOV1978确定的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的保护客体被不断挤压。1983年和1988年,欧专局分别通过Ciba-Geigy案[12]和Lubrizol案[13]确立了繁殖材料和杂交植物可以获得专利保护[14]。美国USPTO上诉与干涉委员会在1985年确认包含高色氨酸的玉米植株可以获得专利保护[15]。但当时的UPOV1978内,植物新品种保护的客体并不包含上述品种。
其次,UPOV1978很难为农产品的全球贸易提供有效的保护。UPOV1978设置的植物品种保护名录以及品种权的行使过少,在跨国性植物新品种侵权保护中并不能起到很好的维护品种权人权利的作用,一定程度上反而降低了育种者维权的积极性,也增加了维权的成本。
最后,因为技术的创新和新技术的运用,UPOV1978已经无法有效激励原创育种创新。从UPOV1978的立法原则来看,基本上是遵守品种权独立原则的,因此UPOV1978很难阻止修饰性育种对原始品种的免费利用,从而失去了激励原创育种创新的功能。
为了应对新形势和更好的保护植物新品种,发展全球农业,UPOV理事会在颁布UPOV1991。UPOV1991废除了植物品种保护名录,并要求成员为所有的植物品种提供保护,避免因不同国家使用不同的保护名录使得跨国性的植物新品种侵权增加。
UPOV1991从分子生物学角度,结合相关理论和技术,深化了“植物品种”的含义,以及植物表型特征与特性基因型或基因型组合间的关联,并且强调植物品种所应具备的特异性、一致性、稳定性是基于某一特定的基因型或基因型组合表达的特性而言的[16]。
对植物品种含义和判断标准的更新完善,实际上也为派生品种制度的引入打下了基础,从侧面反映了生物技术的发展对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完善的影响。
考虑到农产品全球贸易的发展以及专利保护制度的完善与扩展,UPOV1991品种权的保护范围延伸到了实质性派生品种和依赖性品种,这种延伸不仅强化了对原始品种育种者的保护,也尽可能地平衡了原始品种权人和实质性派生品种权人之间的利益。
此外,UPOV1991延长了品种权的保护期限。自授权之日起,育种者所得权利的保护期限不少于20年,较1978版多5年;对于树木和藤本植物的保护期限不少于25年,较1978版多了7年。
UPOV1991出台后,欧共体以其为蓝本制定了《欧洲共同体植物品种保护条例》,UPOV1991的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在“欧盟”范围内得到统一实施[17]。2018年美国修订《美国农业法》,将无性繁殖的植物品种也列为可以申请品种权保护的客体,改变了其自1970年来只有有性繁殖或块茎繁殖的植物品种才能获得品种权保护的历史。
随着UPOV公约的国际影响力逐渐增强,成员也不断增加,截止到2021年2月22日共有77个成员国,其中60个成员国加入UPOV1991,17个成员国加入UPOV1978。中国于1999年4月23日加入UPOV1978。
当前问题与未来发展
虽然UPOV1991较之前的三个版本已经有了比较完善且适应技术发展和农业全球贸易的体系,但还仍有一定的局限性。
农业产品能否大规模商业化种植与育种技术的发展水平和速度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与传统育种技术相比,生物育种技术可以更加精确且高效。
生物育种技术可以突破植物、动物、微生物之间的界限,通过基因的转移、配合、重组,删除不良性状的基因,增加优良性状,并且缩短育种周期[18]。通过生物技术可以加快和提高育种的速度与水平,创造出更适合农业需求的新品种。
根据ISAAA(国际农业生物技术应用服务组织)2019年的统计数据,从1996年开始至今,全球范围内已有30多个国家种植转基因作物,已种植了27亿公顷的转基因作物,1700 万资源匮乏的小农及其家庭总人数超过 6500 万人从转基因作物中受益。

图:2019 Do You Know Where Biotech Crops Are Grown
图源:ISAAA官网
由于这些转基因作物能够应对盐度、干旱、恶性虫害、植物病原体等,因此对未来粮食安全和储存、可持续发展都有积极作用[19]。所以通过生物技术进行植物新品种的培育是现在以及未来植物育种的重要方向。
考虑到上述情况,UPOV1991从基因型或基因型组合角度定义了植物品种,并引入了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和依赖性品种制度,其实就是为了协调平衡生物育种技术应用与传统育种成果之间的利益,从而更好地促进育种创新[20]。
但是植物新品种审查的时间长、成本高的问题依旧没有得到解决。由于植物新品种的特殊性,在审查新品种时需要通过专业测试机构按照特定作物测试指南进行特异性、一致性和稳定性测试(DUS测试)。
DUS测试决定了植物新品种保护体系必须按照作物类别建立门类齐全的技术支撑体系,但是这种测试一般需要经过2到3年的重复观察,期间会受到季节限制、自然灾害、病虫害等影响,同时因为测试的形状多,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时间,而自然条件限制和高成本也使得一些国家很难建立起合适的植物新品种DUS测试。这些都加重了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实施的成本,也就意味着UPOV公约在全球范围内得到推广和一致的难度要比专利制度大很多[21]。
因此,目前国际通用做法是通过UPOV和欧盟主导测试报告国际互认方式解决。但这种互认的方案虽然能解决品种审查环节的DUS测试,却无法解决在侵权救济中的品种及时坚定问题。并且测试报告国际互认并不能解决特定植物品种因环境造成的基因型或基因型组合表达变异问题,同时DUS测试无法发现某些难以反映在植物表型特征上的植物属性。[22]
DUS测试的时间长、成本高也使得植物新品种从申请到授权的时间拉长。美国的植物新品种申请审查平均需要27个月;德国根据植物的种类有不同的审查时间,一般花卉需要4个月到1年的时间,果树则需要4年左右;新西兰的品种权审查从申请到授权则是需要18个月到5年的时间。
我国的植物新品种申请到授权的时间,根据国家林草局的公开数据,从申请到初步审查需要在6个月内完成,但后续的实质审查即测试部分并不能给到具体的时间。根据国家林草局《2021年第11号公告》,授权的2021年第一批植物新品种名单里,最早的是2016年申请的“荣耀”,最晚的则是2020年申请的“新桉11号”。

图:2021年第一批植物新品种名单截图
截图:德同智汇
总的来说,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虽然在不断地完善,也更加明确品种的含义以及判断的标准,但保护和维权的成本还是居高不下,尤其是在测试申请品种是否符合相关要件时,需要品种权人以及测试机构投入大量的时间与成本。
因此,未来对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进行完善时,更加精细高效的测试方式以及DNA分析技术、生物研究技术的发展缺一不可。
我国作为农业大国,种子尤其是优质种子的需求一直很高,加入UPOV1978已有22年,我国制定《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也有24年,但品种增加、技术发展以及与国际农业贸易的不断加强也在推动我国建立更加的完善的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
同时国际上对植物新品种保护是以品种权还是专利权的讨论,国内对中国是否需要加入UPOV1991以及加入后的应对措施的讨论,都是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领域的热点问题。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命脉”,如何更好保护植物新品种育种者的品种权以及更好地利用现代生物技术进行更快更高效的品种审查是未来一个时间内需要各国以及UPOV深入思考的。而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的不断完善也必然能够激发育种者的创新热情和积极性,利用更加高精尖的生物技术培育出更优质的种子。
参考文献
[1]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人民法院种业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典型案例,2021-09-07,责任编辑:刘帆
[2] 李菊丹: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的变革发展与我国应对,《知识产权》2020年第1期
[3] 文二: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的建立,知乎
[4] 张天真主编:《作物育种学总论》,中国农业出版社 2011年版
[5] 李菊丹著:《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6] 二十世纪中期,一些发达国家和墨西哥、菲律宾、印度、巴基斯坦等发展中国家开展利用“矮化基因”,培育和推广矮秆、耐肥、抗倒伏的高产水稻、小麦、玉米等新品种为主要内容的生产技术活动,解决发展中国家的粮食问题,对世界农业生产产生深远影响。
[7] 张天真主编:《作物育种学总论》,中国农业出版社 2011年版
[8] UPOV1961/1972 Art.2(2)
[9] UPOV1961/1972 Art.4(4)和(5)
[10] UPOV1978Art.37
[11] UPOV1978Art.6(1)(b)和(d)
[12] Case T_0049/83 - 3.3.1 [ 1983.07.26 ] OJ EPO 112, Ciba—Geigy:Propagating material.
[13] Case T_0320/87 - 3.3.2 [ 1988.11.10 ],1990 OJ EPO 71,Lubrizol: Hybrid plants ,21 IIC361(1990): Hybrid Plants(1988).
[14] “与美国不同的是,欧洲专利局必须处理欧洲专利与UPOV公约的关系问题因为欧洲专利与美国专利所能保护的植物发明的范围是不同的。欧洲专利所保护的植物发明不包括植物品种的创新,植物新品种仍由UPOV公约下的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提供保护。”——引自李菊丹: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的变革发展与我国应对,《知识产权》2020年第1期,注释18
[15] Ex parte Hibberd, 227 U.S.P.Q.443(1985)
[16] 同注释2
[17] 同注释15
[18] 张先德:《现代农业中的生物技术》,载中国农学会耕作制度分会2004年学术年会会议论文
[19] 项诚、王晓兵、黄季焜:《转基因抗虫棉在中国的推广和传播途径研究》,载《中国生物工程杂志》2016年第11期
[20] 同注释2
[21] 同注释2
[22] 同注释2